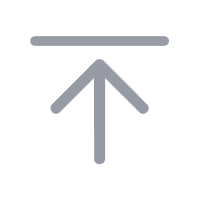舒博韩说我是顾言的完美替身,我笑纳了。只因妹妹高昂的医药费,
我甘愿扮演他心上人的影子。他总在深夜醉醺醺地抱着我,一遍遍唤着顾言的名字。
我咳血晕倒那天,他正为顾言回国举办接风宴。医生宣布肺癌晚期,我默默藏起诊断书。
最后一次见面,他递来机票:“顾言想看极光,你陪他。”我笑着答应,
转身却订了飞往南方的单程票。舒博韩在空荡的公寓里,只找到一本泛黄的《小王子》。
翻开扉页,是我未写完的遗言:“玫瑰驯养了小王子,而我,终于放你自由。
”---消毒水的味道,冰冷,刺鼻,像一根细针,顽固地钻进洛寒霖的鼻腔深处。
他坐在医院走廊冰凉的蓝色塑料椅上,
指尖无意识地抠着膝盖上那条洗得发白、边缘起了毛球的旧牛仔裤。
妹妹洛小雨被护士推进检查室已经快一个小时了,那扇沉重的门紧闭着,
隔绝了里面的一切声响,只留下令人窒息的死寂。他抬起头,
目光空洞地掠过对面墙上褪色的宣传画——一个咧着嘴笑、牙齿过分健康的孩子,
手里举着“爱护牙齿”的牌子。这笑容突兀得近乎残忍。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,
打破凝滞的空气。他掏出来,屏幕上跳动着“舒先生”三个字,像一道冰冷的符咒。
指尖划过接听键,那边立刻传来舒博韩低沉的声音,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烦躁,透过电波,
精准地砸在洛寒霖紧绷的神经上:“在哪?”背景是模糊的杯盏碰撞声和隐约的人声谈笑。
“医院。”洛寒霖的声音有些干涩,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小团砂纸,“小雨复查。
”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,随即是更深的命令口吻,不容置疑:“晚上顾言回国,七点,
蓝山会所,替他接风。你过来。”他甚至没有问一句小雨的情况如何。
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紧,猛地一缩,尖锐的疼痛瞬间蔓延开。
洛寒霖用力闭了闭眼,再睁开时,眼底那点微弱的波澜已被强行压平,只剩一片沉寂的死水。
“好。”他听见自己平静无波的声音回答,“我处理完这边就过去。”电话**脆地挂断,
只剩下单调的忙音在耳边嗡嗡作响。他握着手机,冰冷的金属外壳紧贴着掌心,
那寒意却一路渗透进骨髓里。顾言……这个名字,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,悬在他头顶,
每一次出现都精准地刺向他早已千疮百孔的心脏。走廊尽头的灯管滋滋闪烁了两下,
光线忽明忽暗,映着他苍白的侧脸。他下意识地抬手捂住嘴,压抑地咳了几声,
一股熟悉的、带着铁锈味的腥甜猛地涌上喉头。他猛地站起身,
踉跄着冲向走廊尽头的洗手间。“砰!”隔间的门被他反手用力撞上。他扑到洗手台前,
拧开水龙头。哗哗的水流声暂时掩盖了胸腔里翻江倒海的痛苦。他佝偻着背,
剧烈地咳嗽起来,身体像一张被拉到极限的弓,每一根骨头都在发出不堪重负的**。
他死死咬着牙关,不让那失控的声音溢出喉咙。咳得撕心裂肺,眼前阵阵发黑。终于,
一股温热的液体冲破喉咙的封锁。他猛地张开嘴,
殷红的血点“噗”地一声溅落在纯白冰冷的陶瓷洗手盆里,迅速被水流冲开,
晕染成一片刺目的淡红,如同雪地里骤然绽开的诡异花朵。那红色刺得他眼睛生疼。
他撑着洗手台边缘,大口喘着气,冰冷的汗珠顺着额角滑落,滴进水池,
混入那尚未散尽的血水里。镜子里映出一张脸,惨白得像一张揉皱的纸,
只有嘴角还残留着一点没来得及擦掉的血迹,像一抹诡异的胭脂。
他盯着镜中那个形容枯槁、狼狈不堪的自己,眼神空洞。舒博韩要的,从来不是洛寒霖。
他要的,只是这张酷似顾言的脸,在顾言不在的时候,填补那份空虚。而他,
为了病床上妹妹活下去的希望,早已在这份扮演中,彻底交出了名为“自我”的东西。
洗手间门外的走廊上,传来护士清晰的呼唤:“洛小雨家属?洛小雨家属在吗?检查做完了!
”洛寒霖浑身一震,像是从一场噩梦中惊醒。他迅速掬起冷水,狠狠泼在脸上,
试图洗去所有的狼狈和血污,然后用袖子胡乱擦干。深吸一口气,
他挺直了那仿佛随时会折断的脊背,对着镜子,努力挤出一个平静的、没有任何破绽的表情。
镜子里的青年,眼神麻木,只有嘴角勉强牵扯出的弧度,僵硬得如同画上去的面具。
他拉开门,走了出去。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,每一步都沉重得像是踩在棉花上,
又像是踏在刀尖上。---蓝山会所顶层的VIP包厢里,
空气被昂贵的雪茄烟、香槟酒气和浓烈的香水味糅合发酵,
形成一种粘稠的、令人微醺的氛围。巨大的水晶吊灯洒下过于明亮的光线,
照得每一张精心修饰过的面孔都熠熠生辉,却也显得格外虚幻。
包厢厚重的雕花木门被侍者无声地推开,洛寒霖走了进来。他换下了那身旧牛仔裤,
穿着一件舒博韩助理早前送来的、剪裁合体的白色丝质衬衫,衬得他身形愈发单薄清瘦。
脸上也看不出丝毫病容,甚至薄薄地敷了一层粉底,掩盖了过于苍白的肤色,
唇色也被一点润唇膏点了点,看起来只是有些疲惫的俊秀。喧嚣声浪瞬间涌来,将他淹没。
他下意识地微微蹙眉,随即又强迫自己舒展开,换上温顺而略带疏离的神情。目光快速扫过,
精准地定位在包厢最中心的位置——巨大的环形沙发组上。舒博韩慵懒地靠坐在主位,
昂贵的深灰色西装外套随意搭在沙发扶手上,露出里面的黑色衬衫,领口解开了两颗扣子,
显出几分不羁。他一手端着盛着琥珀色酒液的水晶杯,另一只手,
正亲昵地搭在旁边一个年轻男人的肩上。那个男人,顾言。
洛寒霖的脚步几不可察地停顿了半秒。心脏像是被投入冰湖深处,瞬间冻结,
然后碎裂开无数细密的冰凌,尖锐地刺向四肢百骸。顾言穿着剪裁得体的米白色休闲西装,
笑容温润得体,正侧着头,专注地听着舒博韩说话。
灯光落在他微卷的柔软发梢和精致的侧脸上,整个人像一块精心雕琢、温润无瑕的美玉。
那双眼睛,尤其像,清澈,带着一种不谙世事的明亮。而他洛寒霖……他垂下眼睫,
遮住眼底一闪而过的自嘲。他不过是顾言这块美玉跌落凡尘时,溅起的一点卑微泥点,
被舒博韩捡起来,擦去表面的浮尘,勉强塑成一个影子。他深吸一口气,
压下喉咙深处再次翻涌起的痒意,脸上浮起训练过无数次、完美无缺的温顺笑容,
朝着那个中心区域走去。每一步都踩在自己无声的心跳上。
舒博韩的目光终于从顾言身上移开,落在他身上。那眼神很淡,
带着一种主人审视所有物的随意,上下扫了他一眼,
像是在确认一件物品是否按照要求摆放好了位置。没有询问小雨,没有关心他为何迟到,
甚至没有一丝波澜。“来了?”舒博韩的声音不高,
但在喧闹的包厢里清晰地传入洛寒霖耳中,带着一丝理所当然的吩咐,“去那边坐着,
自己倒点喝的。”他随意地扬了扬下巴,指向沙发另一端,靠近角落的一个单人位。
那个位置,远离中心,远离此刻被舒博韩光芒笼罩的顾言,
像一个被遗忘的、微不足道的注脚。洛寒霖脸上温顺的笑容没有丝毫变化,
甚至更加柔和了几分。他顺从地点点头,声音平静:“好的,舒先生。”然后,
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精致木偶,安静地、悄无声息地穿过人群,走向那个指定的角落。
沙发很软,陷进去却感觉不到丝毫舒适。他拿起桌上一个干净的香槟杯,
旁边的侍者立刻上前为他斟上浅金色的液体。气泡细密地升腾、破裂,发出细微的声响。
他端起来,却没有喝,只是虚虚地握着,冰凉的杯壁贴着指尖。目光不受控制地飘向中心。
舒博韩不知说了句什么,顾言弯起眼睛笑了起来,那笑容干净又明亮,
带着一种被世界温柔以待的纯粹。舒博韩看着他,
深邃的眼眸里漾着一种洛寒霖从未见过的、近乎纵容的暖意。他抬手,
极其自然地替顾言拂开了额前掉落的一缕碎发,动作轻柔得近乎珍视。“博韩哥,你真是的,
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”顾言笑着嗔怪,语气里却满是亲昵。“在我眼里,你永远需要照顾。
”舒博韩的声音低沉含笑,清晰地穿透嘈杂的背景音,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,
精准地刺入洛寒霖的耳膜。他猛地攥紧了手中的香槟杯,指尖用力到骨节泛白,
冰凉的液体在杯中剧烈地晃荡了一下。一股尖锐的刺痛感毫无预兆地从肺部深处炸开,
直冲喉咙。他死死咬住下唇内侧的软肉,
用尽全身力气将那阵汹涌的咳意和喉头的腥甜狠狠压下去。
剧烈的生理反应让他眼前阵阵发黑,胸口剧烈起伏,额角瞬间沁出细密的冷汗。他低下头,
借着昏暗角落的光线掩饰自己的失态,身体微微发着抖。“嘿,寒霖!
”一个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在头顶响起,伴随着浓重的酒气。洛寒霖强行压下翻腾的气血,
抬起头。是舒博韩的发小,陈禹。陈禹端着酒杯,脸上带着玩味的笑容,
目光在他和远处的舒博韩、顾言之间来回逡巡,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和某种居高临下的怜悯。
“啧,正主儿回来了,”陈禹凑近了些,压低了声音,带着酒后的轻佻,
“你这‘高仿’的日子,怕是不太好过了吧?”他故意把“高仿”两个字咬得很重,
像在欣赏一件即将被丢弃的赝品。洛寒霖握着酒杯的手指又收紧了一分,
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。脸上却依旧维持着那副温顺的面具,甚至扯出一个更浅淡的笑容,
声音平稳得听不出任何情绪:“陈少说笑了。”“说笑?”陈禹嗤笑一声,
显然对他的平静反应不太满意,恶意更浓,“我看你挺能忍啊。博韩对顾言什么样,
对你又什么样,瞎子都看得出来。怎么,还舍不得这金丝雀笼子里的好日子?
还是说……”他故意拖长了调子,目光带着猥亵扫过洛寒霖苍白的脸和单薄的衬衫,
“伺候人的活儿,你干上瘾了?”刻薄的言语如同淬了盐水的鞭子,
狠狠抽打在洛寒霖早已麻木的心上。他感觉肺里的空气被瞬间抽空,
窒息感伴随着剧烈的刺痛再次袭来。他猛地站起身,动作太急,
带得身下的沙发都发出一声闷响。“抱歉陈少,”他声音依旧竭力维持着平稳,
但尾音已经带上了一丝无法控制的轻颤,脸色在变幻的灯光下白得透明,“我去下洗手间。
”他甚至不敢再看陈禹那副看好戏的表情,也无力再去看远处那刺眼的一幕,
几乎是落荒而逃,推开包厢厚重的门,将里面的喧嚣、香水味和刀子般的目光隔绝在外。
走廊里相对安静,只有远处隐约的音乐声。他扶着冰冷的墙壁,踉跄着向前走,
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。喉咙里的腥甜再也压制不住,剧烈的咳嗽冲破封锁,撕心裂肺。
他跌跌撞撞地冲进最近的洗手间,反手锁上门。这一次,他连扑到洗手台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身体顺着冰冷的瓷砖墙壁滑落,瘫坐在光洁的地面上。他蜷缩起来,像一只受伤的虾米,
剧烈地咳着,大口大口的鲜血从他指缝间涌出,滴落在白色地砖上,
溅开一朵朵刺目惊心的红梅。冷汗浸透了衬衫,贴在冰冷的皮肤上。
每一次呼吸都扯着肺部剧痛,每一次咳嗽都像是要把整个胸腔撕裂开来。他大口喘着气,
眼前阵阵发黑,耳朵里嗡嗡作响,世界仿佛在旋转。过了不知多久,
那阵要命的咳喘才稍稍平息,只剩下肺部火烧火燎的痛楚和深入骨髓的疲惫。他靠在墙上,
眼神涣散地望着天花板刺眼的顶灯,任由嘴角的血迹蜿蜒流下,滴在白色的衣襟上,
像一片绝望的烙印。口袋里的手机在震动。他麻木地掏出来,屏幕上闪烁着“舒先生”。
他盯着那三个字,看了很久很久,直到屏幕的光暗下去。然后,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,
抬手抹去嘴角的血迹,撑着冰冷的墙壁,极其缓慢地、一点一点地站了起来。镜子里的人影,
脸色灰败,眼神空洞得像一口枯井,只有那抹鲜红的血痕,在惨白的底色上,触目惊心。
他拧开水龙头,冰冷的水冲刷着手上的血迹。水声哗哗,
掩盖了门外隐约传来的、属于包厢里的、顾言那清越愉悦的笑声。---“晚期肺癌,
已经扩散。”戴着金丝眼镜的主任医师放下手中的CT片,语气沉重得像一块铅,
直直坠入洛寒霖的心湖,没有激起一丝涟漪,只有死寂的冰冷向四周蔓延。
他隔着宽大的办公桌看着洛寒霖,眼神里带着职业性的悲悯,“洛先生,情况……很不乐观。
癌细胞转移到了淋巴和部分骨骼,手术意义不大。目前,我们建议先进行保守治疗,
控制病情发展,缓解症状……”后面的话,洛寒霖听得有些模糊了。
那些专业术语——“靶向药”、“生存期”、“姑息治疗”——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,
嗡嗡作响,失去了具体的意义。窗外的阳光很好,透过百叶窗的缝隙,
在光洁的地板上切割出一道道明暗相间的光栅。灰尘在那束光柱里无声地飞舞,
仿佛在进行一场无人观看的、徒劳的舞蹈。他静静地坐着,双手放在膝盖上,指尖冰凉。
出乎意料的平静。没有歇斯底里,没有痛哭流涕,甚至连一丝明显的恐惧都没有。
只有一种尘埃落定般的疲惫,和一种……诡异的解脱感。原来是这样。原来那些咳出的血,
那些深入骨髓的疼痛,那些夜不能寐的窒息感,都是身体在为他敲响最后的丧钟。也好。
他近乎麻木地想。这具早已不堪重负的躯壳,终于可以彻底休息了。
只是小雨……心脏猛地抽痛了一下,比癌细胞啃噬骨头还要尖锐。他放在膝盖上的手,
无意识地蜷缩起来,指甲深深陷入掌心,留下几个深红的月牙印。“……所以,洛先生,
您看……”医生的声音将他从短暂的失神中拉回。洛寒霖抬起头,
脸上依旧是那副温顺得近乎漠然的神情,声音有些低哑,却很清晰:“谢谢医生。
治疗方案……我考虑一下。”他顿了顿,
目光落在医生手边那份厚厚的诊断报告和CT影像上,“这些资料,我能带走吗?
”医生愣了一下,似乎没料到他是这样的反应,随即点点头:“当然可以。不过,洛先生,
我还是建议您尽快和家人商量,确定治疗方案,时间……”“我知道。”洛寒霖打断他,
站起身,动作有些迟缓,但很稳。他接过医生递来的文件袋,很厚,很沉,
像装着他整个生命的重量。他把它紧紧抱在怀里,像抱着最后一点残存的微光。走出诊室,
医院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一如既往地刺鼻。他抱着那个沉重的文件袋,一步一步,走得很慢。
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照进来,暖意融融,却丝毫驱不散他身体里透出的寒意。
经过一个垃圾桶时,他脚步未停,只是将那份诊断报告抽出来,
毫不犹豫地、平静地塞进了那个写着“医疗废弃物”的桶口深处。
白色的纸张瞬间被肮脏的垃圾淹没,只露出一个模糊的边角。
他不需要那些冰冷的文字来提醒他生命的倒计时。那份重量,那份绝望,早已刻进了骨髓里。
回到那个名义上属于舒博韩、他暂住的市中心高级公寓,里面依旧冰冷空旷,没有人气。
他把那个装着CT片、病历本等剩余资料的文件袋,塞进了自己那个半旧的双肩背包最底层,
上面盖上了几件同样洗得发白的旧衣服。做完这一切,他才感到一阵灭顶的疲惫席卷而来,
几乎站立不稳。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。他拿出来,屏幕上跳动着“舒先生”。
指尖划过接听键。“在哪?”舒博韩的声音传来,背景是汽车行驶的轻微噪音,
带着一丝工作后的疲惫,还有……一丝不易察觉的愉悦?“在家。
洛寒霖舒博韩小说<替身无声>全文在线阅读 试读结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