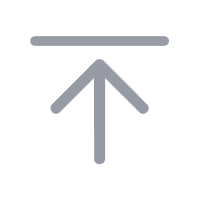许景渊教授(1912-2006)。黑马 | 供图
许大雄《我与〈围城〉中的赵辛楣》记钱瑗临终言:“告诉你一个秘密,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人告诉你了。《围城》中的赵辛楣是参照你和你爸爸虚构出来的。”(《文汇报》,2010年10月9日)“你爸爸”是翻译家许景渊(1912-2006,无锡人,笔名劳陇),钱锺书先生堂大妹锺元之婿。近日钱先生复许景渊手帖流布(许慧辑《槐影庐存牍》,世界联合出版社2025年5月版),其中评骘时贤,笔端振风,简上凝霜,颇趣。
钱歌川
上海《外国语》杂志1984年4月号刊登许景渊《望文生义——试谈深层结构分析与翻译》,谓“钱歌川先生的《翻译的技巧》是一本翻译理论技巧的精湛之作,风行海内外,但是其中有一些译例,似乎也停留在表层结构的分析,恐怕不一定符合作者的原意。下面试从该书中摘引数例, 并略加分析”云云。钱歌川(1903-1990),湘潭人。钱先生1984年5月24日复函许景渊:
顷承赐近作,敝处蒙《外国语》编辑部按期寄赠,早已家中传观,拍手称快。金唱山君留日学英语,回国后其道不行,适胜利后需通晓日语者赴台湾参与高教,渠时运大来,去任台大文学院长兼英文系主任。而好景不常,美国人及美国毕业生蚁聚,遂束置高阁,挂名领薪。不料老年尚能向大陆行骗。渠不足道,适见吾国之土包子易欺耳。君此篇有胆力,有识力,有学问,有文采,破邪抉伪,功真不在禹下也!不才游台时,曾与此君相遇,渠包周身之防,盖疑畏将夺其位也,腐鼠嚇雏。旧事真堪一笑。
“行骗”和“功不在禹下”(《管锥编》道及“禹铸九鼎”,论章学诚“于学人文士之欺世饰伪、沽名养望、脱空为幻诸方便解数,条分件系,烛幽抉隐,不啻铸鼎以象,燃犀以照”;《谈艺录》亦谓“大禹铸鼎”,“铸鼎难穷其类,画图莫尽其变”),那是钱先生照例的夸饰,“下笔又重了”。
1948年春,钱先生作为国立中央图书馆编纂,参与在台湾举行的教育部文物展览会。
钱先生念大学时就爱给人起外号(许振德《忆钱锺书兄》,《清华校友通讯》1963年4月号),和好友熟人弄笔摇舌,每相对作诨语隐语。“金唱山”其一也。《洗澡》里的“都遮着半个脸”的“汝南文”,想是师其狡狯。

钱锺书致许景渊函。
卞之琳
龙公著席:小女归,获读尊论译诗之作,中肯綮,搔痒处,足下于此事可谓升堂哜胾矣!某君乃龚鼎孳司阍所谓“诗蛆”耳,而盗名窃位,遂使公论不申。区区者淫威如许,即小可以见大。曩岁孙大雨撰文纠其谬,《外国语》《译林》皆不敢载。学究酸丁,亦相回护如官场然,世有贾生,得无痛哭流涕长太息哉!
许景渊早在我们编的《记钱锺书先生》里发表《从钱锺书先生学诗散记》(大连出版社,1995年版,第4-17页),迻录了这封信,但隐却“孙大雨”,还专门注解“诗坛巨公并非指个别诗人”,又误释“不敢载”作“不欲载”。
“某君”者,卞之琳(1910-2000)也。“诗蛆”不经见,喻指以诗为利禄之具者。钱先生《霞举堂集》笔记节抄卷七:“龚合肥以总宪守制家居时,士人投诗,日以什百计,阍者往往应接不暇。一日,有士投诗,阍者受置几上。士促之。阍者掷其诗,叱云:‘去,去!汝这诗蛆,也来献诗!’”《坚瓠集》笔记亦札之,并眉批“诗蛆”曰:“千里乎!小趋乎!”
这儿痛恨“官场酸丁”,为孙大雨抱不平,可面对《译林》的编辑,却重贬孙大雨,回护《外国语》:“卞译的风波,[李]良佑同志(编者注:《外国语》杂志主编)上周来长信都讲了。不出所料,我也许是第一个敲警钟的人。《外国语》如此处理,我认为很妥当。孙的刻毒,一半是故态,一半是宿怨,因曾遭排挤也。”态度可堪玩味。“敲警钟”见于钱先生给李景端的信:“卞之琳同志整页的前言,虽说‘正谬指偏’,其实是说他的译文比‘各家中译文’都好。整篇都表示他的译文不同凡响、出类拔萃……假如你利用主编应有的权力,情商节删一些自我吹捧语,也许不会引起读者的笔墨官司。”(李景端《钱锺书信中私房话》,收入《风疾偏爱逆风行》,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,第179-185页)
郑朝宗
北京《读书》1984年5月号重刊林海《围城与弃儿汤姆·琼斯的历史》。1986年张大年把所作《围城新论》稿托钱静汝、许景渊求教于钱先生,钱先生“聊拈三事,以当荛献”:
一、林海乃郑朝宗先生笔名,非李健吾先生,李君当年于拙著忝窃名誉,颇不以为然也。二、斐尔丁云云,学人小说云云,皆本林海文来,颇不中肯。弟于斐尔丁书初不笃嗜,即云有所师法,亦如少陵之“转益多师”,如心理刻划已非斐尔丁所长。苟拙著为“学人小说”,则萨克莱、乔治·爱略脱、弗罗拜、马赛尔·普罗斯脱所著以及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《儒林外史》等皆得称此名矣。此如见人家稍有像样家具陈设,即划属“资产阶级”,或架上有几本线装书及原版洋书,即断定主人“学贯中西”也。
差不多同时,郑朝宗(1912-1998)在家作《怀旧》:“我觉得这样的批评太不公道,便用‘林海’笔名写了一篇题作《围城与Tom Jones》的文章,发表在储安平主编的《观察》周刊上。按照我所理解的作者意图和艺术手法,给此书以比较公允的评价。钱先生起初不知道这是谁写的,后来知道了,十分高兴,说我是《围城》‘赏音最早者’。”
“赏音最早者”之面谀缘自被眼谩,抑“颇不中肯”之背毁由于“文章藻鉴随时去”?疑莫能明。
程千帆
“惠柬、照相及沈书词稿,情重锡厚……公于沈夫人词曾极赏誉,弟于沈翁诗则不甚许可。”此1992年12月25日翰中语。“沈翁”,程千帆(1913-2000)。参看刘永翔《钱通》:“子钱子曰:程千帆之诗‘野野狐’(吴语‘胡乱成篇’之意,较北人语‘凑合’更带贬义),其妻沈祖棻之词稍胜,然闻其佳者多吴瞿安点窜之笔,未足窥其真面目也。”
高阳
《记钱锺书先生》所载1990年12月26日书,许景渊芟夷了末一节——
高某一书乃英美近日所谓“faction”,名为纪实(fact)而泰半臆造(fiction),最足以欺世误人。书名即不甚通,“摩耶”乃梵语maya音译,正是“梦幻泡影”之意,而下接“梦”字,生硬冗复,适见其乔充博学(pretentious)。老眼昏花,可读之书,尚不暇给,实不愿浪抛目力于此等trash。有辜盛情。但兄如猪八戒之自称“猪老实”,于弟前不打诳语也。呵呵!
《梅丘生死摩耶梦》,张大千传记,1984年台北民生报社出版,许景渊表荐的是1988年北京中华书局版。作者高阳(许晏骈)和许景渊同宗。1979年高阳读过《管锥编选录》,作《钱锺书的管锥编》,断言《管锥编》是“刺”书。目光如炬——据栾贵明传言,钱先生曾对《围城》德译者说:“《管锥编》是一部政治著作,不要一开始就把方向搞错了。”(张建术《魔镜里的钱锺书》,《传记文学》1995年1月号)
“猪老实”是钱先生的创造,还见于与黎活仁、文怀沙的尺牍。
罗新璋
罗新璋(1936-2022)的《钱锺书的译艺谈》载在《中国翻译》1990年9月号。十几个月后,许景渊忿愤愬于“大兄”:“罗君,度于大兄趋奉甚殷;此君实欺世盗名之流,未足深信。渠托词宣扬钱学,借以自高身价,其情尚不无可原;但任意歪曲文意,欺蒙读者,则实难于容忍。弟近撰文拟援引《管锥编》中文句,因取罗君大作重读之,以期印证;岂知愈读愈糊涂,深奥莫测;兹将其原文附签注意见附呈,祈大兄明察。罗君自诩博学,攀附名贤,俨然以中国译论权威自居,人亦以此目之;实则其人头脑不清,钻入故纸堆中,不能自拔,恐终必自陷于绝境也。”
钱先生1991年12月24日答复:“所评文兄曾寓目,其香港本较此更多千余言。作者于兄亦极少过往。”讽谕许景渊“不必太‘认真’,莫学《柳毅传》中龙王爱弟钱塘君之仗气发恶,海立潮涌,造成天灾人祸也”,尽管开头要送他一顶“眼光真如岩下电”的高帽子。香港本刊于《中国语文通讯》1990年11月号。钱先生1991年2月10日致函罗新璋:“近香港寄来大作,得见全豹。既佩精详,复惭奖饰,特此修书志谢。”
范旭仑
责编 刘小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