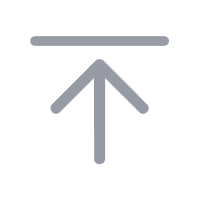一位来北京出差的租客住在一家青旅五人间的一个床位(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/图)
2025年3、4月份,我走访了北京的七八家青年旅社,它们大多位于城市的繁华地段,交通便捷,周围是鳞次栉比的写字楼、大型购物中心或热门旅游景点。
相较于酒店和长租房,青旅有着更为开放和活跃的社交氛围,还有性价比的优势——既提供每晚一二百元、4-5平米的单人间,也有五六十元的床位,在退房政策上也更灵活,因此成为很多年轻人出行住宿的选择。

从一家青旅望去,旁边就是北京CBD核心区的高级公寓(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/图)
在青旅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住客:旅游的、出差的、考试的、实习的、创业的、找工作的、陪家人看病的,还有刚稳定下来、正在找长租房的。“临时感”和“过渡期”是青旅住客身上最显著的特点,一两只行李箱就是此时全部的家当。他们像一群在城市中迁徙的候鸟,短暂地在此停留,随时准备继续漂泊。
我在大厂林立的北京中关村见到了南方姑娘安芳,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,还在试用期内。一头蓬松的卷发,化着淡妆,薄薄的粉底遮盖在微微起皮的脸颊上——北方春季的干燥和柳絮让她感到不适。

小朱在一家青旅的公共区办公,走廊上摆放着住客临时存放在前台的行李。作为一名金融行业的创业者,小朱为了方便联系客户而选择了这家位于北京国贸地区的青旅(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/图)
35岁的安芳来京将近两个月,她把公司周边二三百块的酒店都住遍了,也在附近看过不下三十套房子,最终还是选择了青旅。
“我对住宿的环境有一点挑剔,一开始我想租一间一居室,但海淀这边的房租确实蛮贵的,于是考虑合租。那段时间我天天下班后就去看房子,最多一个晚上看了十套。有几套还比较满意,但不能保证跟我同住的人是否带人回来住,虽然平台限制每个房间只能住一个人,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住两个,甚至更多人。出于安全和个人隐私的考虑,我还是放弃了。”

林云在一个多人间里打扫卫生,来自邢台的大四学生小刘正在床位上准备简历。小刘即将毕业于网络工程技术专业,目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实习,租住在单位附近的这家青旅(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/图)
安芳在网上看到这家青旅的好评率高,经过实地考察,对卫生状况、设施和居住环境都比较满意,她才确认了订单。虽然是公共淋浴间和卫生间,房间“很窄很小”,一个月的住宿费跟合租的房费差不多,但这里不用额外支付水、电、煤气和宽带费,也没有押金、服务费和违约金,随时可以“拎包走人”——最近几个周末,安芳都选择退房去郊外散心。
入住后,隔音是安芳面临的最大难题。虽然前台赠送了耳塞,并规定晚上10点以后减少公共区的噪音,但由于她的房间靠近洗漱区,还是能听到水声、吹风机或烘干机的声音,还遇到过隔壁在夜里唱歌和视频聊天的,好在经过工作人员的沟通都及时解决了。
2024年,因为遭遇职场霸凌,安芳选择了裸辞,即便她在那家头部公司已经入职十年。安芳坦言那段时间“心态崩了”,陷入了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,也切身感受到人情冷漠。“我要离开,去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。”蛇年春节过后,安芳成了一名“北漂”。

林云、张平一家三口(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/图)
在上一份工作中,安芳的日常轨迹是从家里的地库到单位的地库;微信未读999+,有回不完的工作信息;平时加班,周末在家写总结,从没休完过年假。
新的工作还是会加班,但陌生城市的新鲜感让安芳感到舒适和自由。她现在每天步行通勤将近一小时;周末跟朋友相约郊游、购物或者打卡网红餐厅。“北京,真是个机会和容错率高的城市,希望我能重新找回热爱生活的自己。加油。”她在社交平台上写道。

来自绵阳的Echo(左)和来自广州的头头星在一家青旅的走廊化妆。她们约好一起来北京看演唱会,为了减少路途耗时,提前预订了这家在场馆附近的青旅(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/图)
“北漂”的年轻人对大城市的向往,交织着梦想与现实、激情与挣扎。这种向往既源于大城市独特的魅力,也折射出这些年轻人对人生可能性的追求。
鑫鑫在青旅的一天从下午4点开始,醒来后洗个澡,出门抽支烟,然后坐地铁去工作的小酒馆。他负责酒馆外场的服务工作,下班一般在凌晨三四点,再搭乘夜班车回来。
在青旅住了两个多月,鑫鑫决定一直住下去。“性价比高,很适合我们这种月光族。”他住在一个三人间,对住宿的要求就是有个床位能睡个觉。
20岁从内蒙古来到北京,鑫鑫“北漂”七年换过五六次工作,都是从事服务业。“对我来讲,学历是个问题,初中毕业留在老家看不到任何未来。来北京算是一种执念。这里是首都,一个充满梦想和机遇的地方。当年一直想要去看看外边的世界。”

鑫鑫租住在一家青旅三人间的一个床位(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/图)
毫无规律的饮食、昼夜颠倒的作息加上好酒的性格,给鑫鑫的身体带来不可逆的损伤,体检时医生开玩笑,“你这个年纪怎么脖子以下、腰以上没有一块好地方?”从中学开始的焦虑和抑郁也如影随形,时常让他备感压力。
这些年在工作中结识的三位小伙伴是鑫鑫“在北京唯一的精神慰藉”。他们时常相约旅行,在北京每周都会聚一次,“帮我梳理近期的事务,排解压力。在需要的时候,毫无保留地给予我经济上的帮助。”有一次鑫鑫要换手机,一位朋友直接把新办的信用卡递给他。这种信任和情谊像坚固的铠甲守护着鑫鑫,他把朋友称为“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”。

鑫鑫在一间酒馆工作(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/图)
舒缓压力的另一种方法是旅行。鑫鑫常常临时起意,在中国地图上随机选择目的地。对他而言,在西安的鼓楼站一下午和去大连的星海广场喂鸽子一样,换个环境放空自己就是最好的解压。
“我坐在那里吹吹风,看着人来人往,就很安逸。”鑫鑫希望自己处于一种旁观者的状态,观察生活中的“小确幸”。“我不太想局限在一个地方,如果你单纯地因为生计去考虑一些问题,难免会麻木,会计较很多生活中本来不必在意的事情。”因此,他不想被一纸租房合同束缚,而是选择了更为灵活的青旅,可以随时出发。

来自西安的小凯在一家青旅的公共区休息,手里的面包是他当天的晚饭。他来北京将近两个月,曾在商城当过礼仪接待,最近刚入职一家文化经纪公司。北京快节奏的生活让他感到既疲惫又充实(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/图)
2025年4月,我来到位于北京西北五环外的一家青旅,店长林云正在打扫卫生。她干活麻利,不到半个小时就收拾好一套房:更换上下铺的床单被罩、整理床铺、拖地、打扫卫生间和公共区域,离开时顺手提起地上的一大袋垃圾。
林云夫妇经营的这家青旅,一共有四套房,以多人间为主,每个床位每晚30-50元。林云打扫房间时,丈夫张平带着一岁半的宝宝穿梭在各个房间,他手里的电话不停,大部分是咨询房间的,也有退房后落了东西联系取回的。宝宝还走不利落,摇摇晃晃地跟在爸爸身后。转眼到了下午,登记入住的高峰期,宝宝喝着奶在一个床铺上睡着了,夫妻俩正在忙,让我帮忙看一会——平时,他们忙不开的时候也会把孩子交给相熟的住客照看。

藏族小伙阿扎在自己的床位休息。来北京一年多,面对陌生的环境加上语言不熟悉,他有段时间“连吃饭都成问题”,后来经人介绍在三里屯的一间酒吧做安保工作。“我一路走来挺辛苦的,在酒吧能让自己放空,不去想任何事情”(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/图)
2024年刚开店时,他们还不会在网络平台登记房间信息,导致第一位住客“独享”了一套六人间七天之久。为了节约成本,夫妻俩当时分别住在男女房间的床位,林云带着宝宝睡稍大一点的床。每天接触不同的住客,宝宝也变成了“小社牛”,不哭不闹,看见人就笑,还主动打招呼。
如今,这家青旅积累了不少回头客,李莉每次来北京出差都住在这里。“离地铁近,房间也干净,店长特别热情,我每次来都跟她聊天,有种回家的感觉。”

一家青旅的晾衣区(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/图)
林云见识过不同类型的住客,有上班族、建筑工人、学生、游客,还有足不出户的“大仙儿”——每天在房间打游戏,三餐都叫外卖。大多数都“规规矩矩”,偶尔也有让她头疼的,比如夜里在房间不停地打电话或吸烟。“前两天刚赶走了俩,在房间影响别人,提醒也没用,我马上给他们退房费,接待不了。”有的人会因此在平台上写差评,这也是林云最担心的,因为差评会直接影响旅店在平台的页面流量和入住率。
林云夫妇是来自山西运城的“90后”,他们曾在陕西榆林的山区开过面馆给运煤的货车司机供餐、在天津卖过刀削面、在北京做过家常菜。林云觉得,比起开餐馆,经营青旅更累一些。“餐馆是身体劳累,白天忙完,晚上坐那数钱就行了。开青旅是身心都累,每天打扫、换洗、处理各种矛盾,然后还怕他住完给你一个差评。”

藏族小伙阿扎经常骑共享单车通勤,他说自己最擅长的还是骑马 (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/图)
夜幕降临,我离开林云夫妇的青旅,步行几分钟就到了一座大型购物中心。正值周末,这里被璀璨的灯光包围,变成人潮汹涌的不夜城。我刚刚遇到的年轻人——那些折叠城市中的临时住客,是否也曾在某个加班后的夜晚,沉浸在这片沸腾着烟火气的声浪和光影中。
(文中人物除鑫鑫外,均为化名。)
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
责编 郑洁 方迎忠